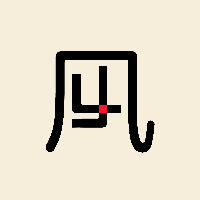这十天,在湖北最西边的小镇上发生了什么


独家抢先看
几天前,当二叔和小镇上那些弯着腰的婆婆人生第一次戴起口罩时,他们都会一遍遍地提起那晚在小镇上空炸响的冬雷。
我是在腊月前来到这座小镇的。跟着帮别人搭灵堂、唱孝歌的二叔,走进这个湖北最西边的角落,也走进大山深处,那些面临着最终离别的家庭。此前,脑海中一直有一个画面。除夕夜的山里,有人刚刚去世,灵前放着火盆,二叔在火盆前唱歌。凌晨将到,山下的小镇升起万千烟花。
比烟花早了几日从天而降的,是深夜里的一串冬雷。那晚,二叔也在山上唱歌。凌晨时分,山谷中突然亮起闪电。
白亮刺目的闪电一道道穿透窗户,接着一串又一串响雷在午夜前后炸响。惊心动魄的雷声,把许多人从睡梦中惊醒。在镇上长到六十多岁,二叔不曾见过冬天打雷。更老的婆婆也是。
小镇上有两条江,一条叫前江,一条叫后江
封城前的去与留
冬雷落下的那天是2020年1月22日。
当天,高速路数据显示数千辆武汉车牌的车辆驶入利川城。这座位于湖北最西边,人口不足百万的小城是避暑胜地,人称武汉后花园。
信息在网上传开已有两天,一直觉得生死这种大事是命里早就定好的。直到雷声落下的那天,才开始有些紧张,念叨着要买口罩。网上已断货。二娘不觉是多大的事儿,说镇上药店里口罩充足,本地人没有买的。下午我骑车去了镇上,七八家药店一一走遍,口罩已一个不剩。
那天,镇上罕见的出现了堵车。腊月二十八,年关将近。各地车牌的车子在路上排起长队。推着行李箱,刚从公交车上下来的年轻人和背着背篓来买年货的本地人,把街上挤得比集市还热闹,没人戴口罩。不知小镇上已被搬空的口罩,都去了哪里。
比起没有口罩,更大的恐慌来自二叔。
疫情的消息,第一时间就告知了二叔和二娘。二娘和大姐最初有些不以为然,觉得这里偏僻得很,什么传染病都不会来。
我从非典讲起,从最初的传播到病愈者的后遗症,再加上二娘自己看手机也看到讯息。二娘的态度很快转变,只是二叔的口头禅依然是“不怕”和“没事”。
二叔不怕,我却怕得紧。主要是因为二叔的工作。
每次电话响起,二叔就会搬着搭灵堂的板子上山去,有时还会连唱几晚的孝歌。葬礼上本就人多,外地赶来的也多。主人家招待一日三餐,租用的公共碗筷上常有黑斑。
腊月和正月最冷的时节,电话来的最频繁。打来电话的多是乡亲。疫情扩散,即使在这偏僻的小镇,也已人人自危。一旦再有电话打来,二叔会怎么选择?我心里没有底。但我知道,如果继续像之前那样,一旦镇上有了确诊病例,二叔和跟着二叔跑的我,都是绝对的高危人群。
一把锤子、一把剪刀,二叔随身的工具
第二天,腊月二十九。年前镇子上的最后一个集市。二娘一早去隔壁借了几只口罩。二叔拖着一车的板子上山了。电话是昨晚半夜打来的。
口罩不是外科口罩,更不是N95,但二叔还是戴好,并照我教他的那样,压了压鼻梁。早上落了雨,山上起了雾。我们在山上转了几圈,那个地方不好找。最后车子停在路边,搭灵堂的木板被葬礼上帮忙的人,一件一件搬了下去。
灵堂前已聚集了不少人。只有我和二叔是戴口罩的。陆续赶来奔丧的人里,本没有戴口罩,却在看见我和二叔后,从衣兜里掏出了口罩。木板太重,二叔需要别人帮忙,免不了要和别人说话。口罩时不时落到鼻孔下。二叔不理,甚至直接把它拽下。
前一天就和二叔说过,不要和外人说话,也不要在人家家里吃饭,灵堂搭完就走。但那天一直忙到下午一点多钟。暂时还没有车子送我们下山。我跟二叔早餐都没有吃。主人盛情留饭,二叔没有拒绝。我端起饭碗退到人群后,二叔吃饭向来慢,又喝起酒。跟一桌不知从哪里来的人,说说笑笑、吃吃喝喝一个多钟头。
就在那天上午,武汉开始封城。
二叔的工作看来是不会停下,他的习惯又一时无法改变。没有任何有效防护装备,吃住都在二叔家的我,开始有些焦虑。
武汉医疗资源紧缺的消息已经传开。这是湖北最偏的地方,医疗资源没法和武汉比,镇上的人卫生习惯和预防措施都不够,一旦有感染,情况绝对会比城市可怕。
我有了暂停拍摄,去外面避难的打算。是去更偏、人更少的山上找个临时住处,还是去市里租个单独的房子,亦或是直接搭火车回山东?那个下午接了老家几个电话,都在催我回去。可是,即使离开也要等到除夕夜,烟花拍完之后吧。惦记了很久的那一刻,终究舍不得。
很严肃的再次跟二叔强调疫情的传染性和严重性,他依然笑嘻嘻地说没事,说他不怕,笑我胆小。我的焦虑终于爆发,冲他大吼一次。
那天晚上,与二叔一起唱孝歌的舅舅他们去了另一座山里。他们将在那连唱几晚的歌,包括年三十和初一。二叔推掉没有去。
那天晚上凌晨十二点,继武汉封城14个钟头后,利川也宣布了封城的通知。半夜两点多看到,反倒安心了。哪里也去不了,也就不用在去与留、逃与不逃之间纠结。
天亮了,除夕到了。早上跟二娘说了封城的消息,商议要不要去超市囤点米粮。二娘觉得没有必要,家里有新打的一百斤稻谷,屋后的山上都是白菜、萝卜,平时吃不完都砍来喂猪的。
那天没有公交,路上也没有车子,与二娘和二叔爬山,去二叔的儿子家吃饭。看到山上一片片青翠的菜田,稍稍放下心来。
镇子的四周都是山,山上有人家,镇子在山下
背锅的,还有老鼠
大抵是知道二叔的工作和脾气,山上的儿子和儿媳也对二叔苦口婆心的劝告。聚餐已用起一次性碗筷,且第一次使用了公筷。第二天,二娘便把公筷的使用推广到自己家里。
二叔看着锅里多出的三双筷子,笑说跟神经病似的。我跟二娘大笑不止。二叔一不小心就把自己的筷子伸到锅里,被二娘敲回,忿忿地多夹菜到碗里,再不把筷子往锅里伸。吃过饭,就是熏白醋与消毒水拖地。
除夕夜终于到来。
开着电视放着春晚,二叔、二娘和我一人抱一只手机窝沙发上不停地刷信息。没人看的电视很快被二娘关掉。天黑后,爆竹声响过,二娘说,烟花要到十一点过后。
镇上产的烟花一向让小镇人自豪,不少人跟我提过除夕夜烟花盛开,以及以前家家户户做烟花爆竹的盛景。提前选好拍摄点,一处在江边,看得到烟花与水中的倒影,还有桥上偶尔亮着灯过往的车辆。一处在山上,俯瞰人间烟花万朵的感觉。
十点多就出门等着,路上没人,江边还有一盏路灯亮着。等到十一点多,烟花突然从四面燃起,一朵比一朵开得大。几次转身又停下。眼看山上的那一处已经赶不上,且深夜里还有七八十度的陡坡要爬。
骑着自行车不停地赶路,烟花一朵朵在头顶,在眼前,在身后,360度的绽开。在繁盛的烟花底下穿过半个镇子。
猫大姐姐从海峡对岸发来信息——
“放的比台北101还要多呢”
山上的那一处终究没有赶上。
想起旧时燃爆竹驱年兽的传说,不知病毒会否被小镇轰轰烈烈的烟花爆竹吓跑,但因疫情阴霾了几日的心,此刻已被烟花照亮。不知舅舅他们正在哪一处的山上唱着歌。假如没有这场突如其来的病灾,二叔应该也会在那里吧。
初一早上,门一开,二叔就溜去对面,站在马路上和那家人说话,被二娘大声喊回。那一家就有从武汉打工回来的。二娘的叮嘱,二叔转头就忘了。
这几日,陌生人一靠近,我就掉头转身,如避洪水猛兽。不得不和人说话时,也刻意退后保持距离。相较之下,二叔依然天真烂漫,见到人仍亲切的想要靠近。
这里的人于我本就是陌生人,但对二叔来说,那是他的乡邻。在这之前,邻居们时常话家常,去谁家赶上饭点,端起碗便吃。
为2020年开年的病灾背锅的,不仅有冬雷,还有老鼠仔。每当我和二娘扯着嗓子纠正二叔的不好习惯时,二叔就会歪过脑袋,大骂老鼠。”都是老鼠仔惹的祸,爱打洞、偷粮吃的老鼠仔,逢到鼠年一定没好事”。接着,二叔跟二娘提议,要不要买上两千斤稻谷,以防鼠年有灾荒。
二娘断然否决。
这天晚上,二叔给平日里一同唱歌的伙伴打电话,劝还在外面唱歌的他们注意一下。大概是被他们笑话了,二叔挂了电话,罕见地和二娘吵了一嘴。不一会,二叔又接到电话。
镇子上有人过世,搭灵堂的时间推到了明天早上。没有人说,这个时候不要去了。我也没说。
掉落的口罩与手上的伤疤
利川已经有了确诊病例。除了超市,水果店都关门了。囤了一堆水果等着过年卖的店老板,正在低价处理水果。
那个晚上很晚没有睡着。二叔做出了他的选择,而我也要做出我的选择。要不要继续跟拍?我本来以为自己有去或者不去的选择,后来发现,无论去还是不去,一旦二叔感染,我都逃不掉。不过是过来拍个片子,出个门怎么还要备好视死如归似的心情?
第二天,二叔扛着竹竿走在路上。路上不见一个人,路两侧的房子里却传出各家的声音。有的在煮早餐,有的在跟小孩子玩。空无一人的街上,家家户户的声音清晰地传出来。窗户上时有露出的脑袋,高声问二叔,又是谁家有人去世了。
刚贴上的红色春联,被白色的挽联遮住。
二叔钻进屋子,我跟着,刚要探头进去,被二叔轰出。“出去,出去,里面人多”。那个上午,二叔一直念叨着一句话,“红事可以推后,白事要怎么办呢?总得要抬出去啊”。
没有爆竹,没有戏班,没有四处赶来的亲友,没有大摆的酒席,在二叔这些镇上的人看来,这老人家真是走得没有福气。于是,再不能没有一个灵堂。
门前来来去去,无论是煮饭的大妈还是帮忙的年轻人,全都戴着口罩。但当大锅的面条煮好后,大家还是一拥而上,端着公用的碗筷抢着捞面条去了。这次,二叔没有去。
他的口罩还是动不动就掉下来,和人说话时仍和平时一样靠的很近。我提醒几次。在外面站久了,手脚冰冷。平时都会去火盆边烤烤火。可火盆前一向人最多。这次不敢凑过去了。
二叔的口罩又一次掉下来。火气一下冒上来,说啥他都不听,回去算了,不拍了。气鼓鼓地从二叔身上摘下小蜜蜂,这时看到他的手。手背上不知什么时候划破一块,血不流了,但干涸的血迹还粘在上面。那一刻,所有的委屈和怒火,一下消散了。
但还是回去了。回去的路上,看见早上走过的路口已被各家的拖拉机、推土机和汽车堵住,不允许机动车辆穿过。
这些天,每天的心情如过山车般,跟着疫情也跟着二叔上上下下。他会不会出去?口罩有没有戴好?一举一动都影响我的心情。对疫病的恐惧,化为了对他人的恐惧。从没有一刻,我们与他人这样的遥远,也这样的命运相连。
而我还有另一重记录者的身份。在介入与旁观之间,当有可能影响自己安危的时候,我是否已经越线?
一个人坐在屋子里,沮丧得很。突然窗帘后传来扑腾声,一只小麻雀不知怎么钻进屋子里,惊慌地急起急落。若是平时,马上捉它出去了。那一刻,却坐着,想听它继续扑腾一会。
一会,屋子里又静下来,雀儿不知躲去了哪里。终于站起来,煮饭。然后,把房间的门打开,去找二叔。
回来后,让他先去洗手,再在手背上贴一枚创可贴。饭已煮好,炉火燃起,那只麻雀不知什么时候自己飞出去了。
远方的朋友时有问候。开始时,还会把自己的焦虑说出来,没有正规的防护口罩,却不得不出门。
再后来,有朋友问起,我只发山上的照片给他们看,说,山上有青菜,山上有泉水,山上还有烧不尽的柴。只要还有春天会发芽的菜种子,就什么都不缺。哦,对了,山下的江里还有鱼。
初三,二叔休息。二娘和二叔提着一兜纸钱上山,要烧给过世的父母。与二叔一前一后走在山间的小路上,二娘想起自己过世的父亲,“他生前就喜欢热闹,喜欢在路上走。他的墓刚好也在路旁。山上的空气多好。”
隔壁,不知是谁家的墓前长了一棵好精神的大叶子草。路过已过世的大哥家的菜园,二叔和二娘进去割了一把菜。用装纸钱的兜子,拎着下了山。下山的路上,一个人影和车影都没有,二娘拎着一兜青菜,脚步轻快地说,回去就把饭焖上。
二叔一进门就拿着香皂洗手去了。屋后的乌瓦房里正透着白色的轻烟,是熟悉的柏树枝子的味。腊月都过去了,谁家还在熏腊肉呢。
作者孔丽丽,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电影学硕士研究生、凤凰网文化创意频道特约研究员。
曾担任《河西走廊》、《金城兰州》、《重生》、《新华书店》等历史类纪录片的策划、撰稿工作,为纪录电影《粤韵芬芳》文学编剧。
原标题:《看见从天而降的冬雷,也看见内心的起落——在湖北最西边的小镇上》
“特别声明:以上作品内容(包括在内的视频、图片或音频)为凤凰网旗下自媒体平台“大风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videos, pictures and audi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the user of Dafeng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mere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pace serv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