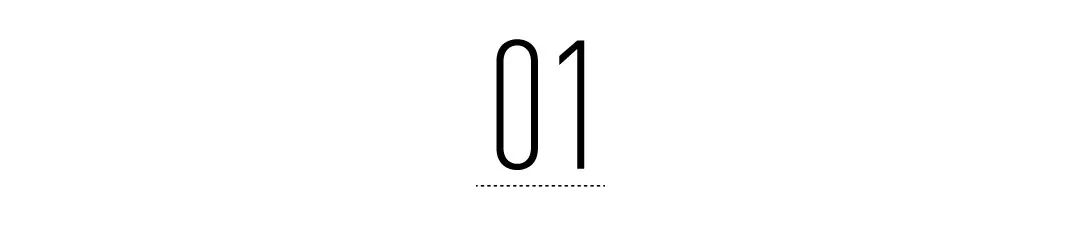不听英国摇滚的人,没有文艺的资格


独家抢先看
1990年,美国佐治亚州坎伯兰岛,滚石乐队演出现场。该图由知名摄影师安妮·莱博维茨拍摄,她自1975年起跟拍滚石乐队巡演。(图/Annie Leibovitz)
英国摇滚常常被“低估”。它塑造品位、视野和想象力;而它的文艺范儿,为王菲们提供了表达方式和技巧上的精确实践路径。
2014年5月3日,张曼玉以“摩登天空签约歌手”身份站上北京草莓音乐节的舞台,演唱《甜蜜蜜》。不那么在调上的低沉嗓音与肆虐通州运河公园的八级大风搅在一起,被网友评价为“女神的车祸现场”。
但张曼玉的合作者们却对这把独特嗓音的源头并不陌生。“重塑雕像的权利”乐队吉他手华东一听到张曼玉录制的小样,就问她是否喜欢英国后朋克乐队“苏可西与女妖”(Siouxsie and the Banshees),张曼玉显得十分激动:“我就是听着他们长大的。”
上世纪70年代,张曼玉在英国读中学,亲身见证以朋克、后朋克、华丽摇滚为代表的听觉风潮席卷世界。
中国的更多普通文艺青年/前文艺青年则是通过音乐网站、电骡、盗版碟甚至打口磁带辗转认识这些生僻概念,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闭幕式直播期间,伴着“烂总”“牙叔”“泡儿”的出现,数度飙泪,高呼“爷青回”(爷的青春回来了)——尽管,在他们的潜意识中,英国摇滚只是五光十色的霓虹灯,鲍勃·迪伦、莱昂纳德·科恩们才是永恒的丰碑。
张曼玉无疑是草莓音乐节的亮点。/图虫创意
乐评人李皖坦言,自己曾经对披头士、滚石乐队持保留态度:“当时觉得摇滚乐还是应该猛烈、尖锐,应该兼具批判性和深度,所以披头士那些清新的爱情歌曲吸引不到我。滚石看上去似乎是坏孩子的形象,可‘坏孩子’也只是人设而已。更重要的是,与沾着泥土气息的三角洲布鲁斯相比,滚石着实显得二流。”
根据李皖的描述,英国摇滚常常被“低估”:你很难列出一位伟大到足以超越专业、国别、时代界限的精神偶像,却不知不觉间被它塑造品位、视野和想象力;无论是王菲、“达明一派”还是你隔壁班那几个嚷嚷着要玩乐队的毛头小子,都可以在它的点拨下迅速高大上起来,“这恰恰是因为它为‘文艺范儿’提供了表达方式和技巧上的精确实践路径”。
以下是李皖的口述。
什么是“英国摇滚”?
提及英国摇滚,浮现在大多数读者脑海中的第一个想法也许是:你是想谈Britpop,也就是英式摇滚吗?这股从1980年代持续到21世纪初的风潮,确实塑造了普罗大众对英国摇滚的最初印象。但在我看来,从1960年代开始,英国摇滚就处于一种“高潮迭起”的状态,它始终吸纳来自其他文化的营养,也对其他文化造成影响。
所谓流行音乐,是以人类所有音乐为素材,在现代主义的激发下进行融合、活化的产物,并与城市化和工业文明息息相关。从这个角度看,流行音乐在战后经济发展登顶、获得全球影响力的美国实现最初的爆发,并不出乎意料。英国自然也在美国流行音乐的辐射范围之内,披头士早期那种少年感极强的唱腔,就带有很鲜明的黑人发声特色。
有意思的是,1960年代,披头士、滚石、“谁人”(The Who)乐队带着他们布鲁斯味儿浓重的音乐,“反攻”了美国,造成“英国入侵”(British Invasion)的文化奇观。除了将“一线流量”的位置包圆,这些英伦乐队的粉丝们展示了什么是追星、粉丝的力量有多强大,而“青少年文化”概念也渐渐浮出水面。
《披头士乐队:回归》剧照
以此为起点,将原本诞生于美国的音乐风格丰富、改良并发扬光大,成为早期英国摇滚乐发展轨迹的重要特色。首先值得一提的是“齐柏林飞船”乐队和“黑色安息日”乐队掀起的重金属风潮——用粗糙、浑浊、颗粒分明的嗓音和更注重音量、速度的器乐演奏,把布鲁斯的原有特色加强到“躁”和“燃”的层面。
其次就是朋克。与曾经和安迪·沃霍尔合作的美国乐队“地下丝绒”相比,“性手枪”、“冲撞”(The Clash)乐队实在称不上先驱。但后二者才是真正使得朋克蜕变为一场成规模的运动的引擎,而且提供了对抗主流的范本:痞、逗比、暴烈、真诚——我创作力匮乏,编曲简陋,乐器能力业余,但我有初心啊。你看,这和现在那些流行朋克乐队的玩法是不是一模一样?
除了朋克和重金属,1970年代见证了英国摇滚乐意义最深远的裂变和探索。平克·弗洛伊德在专辑《月之阴暗面》中玩起合成器,艺术摇滚乐队“洛克西音乐”(Roxy Music)键盘手布莱恩·伊诺单飞后,和德国乐队“发电站”(Kraftwerk)、“橙梦”(Tangerine Dream)不约而同地摒弃传统乐器,利用计算机制造的非自然声响创作。
朋克则蜕变为后朋克,从身体转向内心,或者说从外在的企盼转向精神分析,冰冷、阴郁、颓废、凄美,甚至有种歇斯底里的、病态的色彩。
我认为这是对英国摇滚而言意义重大的十字路口:有一部分在风靡德国、美国的工业金属(以德国“战车”乐队、“九寸钉”乐队为例)和动辄混搭歌剧、交响乐的北欧艺术金属中开枝散叶,变得更“黑”、更“重”;另一部分像“新秩序”或“杜兰杜兰”(Duran Duran)乐队那样,与合成器联姻后,迅速脱胎换骨为温暖、浪漫的合成器流行乐(Synth-pop)。
后者非常受欢迎,因为缤纷的电子舞曲节拍一起,属于城市的时尚气息就扑面而来,很起范儿。
与此同时,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英国出现了一系列独立唱片公司。它们可能本质上不过是青年文化群体,但是都有鲜明的美学体系,以极其含蓄、艺术的姿态示人。以中国粉丝非常熟悉的4AD为例,其封套设计抽象、朦胧;曲风神秘、缥缈;歌词诗歌化,并且极少印在内页上;歌手嗓音走唯美路线,刻意不清晰咬字,放出的照片则总是仙境既视感。
1995年,王菲举办“最精彩的演唱会”。
4AD赋予王菲的,就远远不止她翻唱的几首“极地双子星”(Cocteau Twins)乐队的作品,还包括被粉丝们奉若神明的高级感,比如《寒武纪》《阿修罗》里玩的那种跳脱的概念;比如“大风吹,大风吹,爆米花好美”“太阳上山,太阳下山,冰淇淋流泪”之类不知所云但听上去很酷的歌词;比如她在传媒面前沉默寡言、惜字如金的做派。它们无一不在与大众审美划清界限。
1990年代之后,4AD深海潜水般寒冷、坚硬、幽闭的内核逐渐融化,取而代之的是光明、和煦的氛围。“越来越敞亮”同样是英国摇滚带给公众的感官印象,世纪之交出道的“酷玩”(Coldplay)乐队、“特拉维斯”(Travis)乐队等甚至频繁制造人气金曲,你去KTV里也可以点一首《黄色》(Yellow)或者《懦夫》(Creep)过过瘾。
但什么是“英式摇滚”(Britpop)呢?是要具备“绿洲”乐队那样猛烈、爽脆的吉他演奏,还是要像“电台司令”(Radiohead)乐队那样专注玩科技?或者演唱者的英式口音本身就是最好的标识?通过这些微妙的问题,你会发现英式摇滚的骨骼仍是后朋克的延展,但其皮肤上附着的元素,已经相当丰富了。
从感官上准确触及
个体在现代社会的精神处境
中国的摇滚乐听众其实是个奇怪的群体,与经典摇滚乐作品相关的历史事件、情境发生时,他们并不在场,也没有记忆传承,换言之,他们是在与具体时代失联的状态下理解摇滚乐的。我也是在了解战后流行音乐发展的整体脉络之后,才领略披头士的优秀之处。
在我看来,他们在演唱时情绪的外化是自然、纯粹、喷薄而出的,歌词也有一种模棱两可的叛逆性,一种包裹在嬉笑之下的坚韧——用童谣般诙谐、俏皮的语言表达讽刺,以爱情为载体叙述人、社会、宇宙之类宏大的主题,可批判可娱乐,可走耳可走心,随你怎么理解。这样面目柔和、圆润、妙趣横生的反抗,是非常迷人的。
英国摇滚的“后劲”为何如此巨大?我们不妨审视一下它背后的强大传统:除了古典音乐,还有杂耍、民间戏剧,即类似于中国地方戏、曲艺的表演形式;苏格兰、爱尔兰民谣给予它的灵感更是浩瀚如海。更重要的是,作为工业革命的摇篮,英国的都市文化在上世纪后半叶已经高度成熟。与美国流行音乐图谱中驳杂的乡村、工厂、公路、小镇风景相比,英国摇滚更显精致讲究,别有洞天。
比如,英国摇滚极其注重视觉符号的引入,让旋律影像化。与其说“华丽摇滚”(Glam Rock)开创了新的音乐风格,不如说它的意义在于升级摇滚乐的叙事形式,你看大卫·鲍伊五彩缤纷的发色和妆容,还有他特别喜欢的流苏和亮片,会不会更像时尚icon?他摒弃了以往民谣歌手在演唱中突出自我的路数,转而进行角色扮演,然后把这个角色在作品中持续深化。
1978年,演出中的“性手枪”乐队贝斯手席德·维瑟斯。(图/Bob Gruen)
我再举两个与华丽摇滚无关的例子:平克·弗洛伊德的专辑《动物》并不好懂,但人人都记住了他们在伦敦巴特西发电站上空放飞的巨型粉红色充气猪;“性手枪”乐队贝斯手席德·维瑟斯(Sid Vicious)的爆炸头、铆钉皮夹克和挂着锁的大铁链子,现在成了朋克艺人的标配。总而言之,通过英国摇滚,你能够感受到摇滚并不是孤立的艺术门类,而是和表演、现代设计一道,在更为宽广的大文化领域内水乳交融。
英国摇滚也能从感官上准确触及个体在现代社会的精神处境。后朋克听上去如此“负能量”,其风格却仍然被各国音乐人借鉴,实现某种意义上的“流行”,我认为原因在于:
全球化背景下,所有人的思想状况和经历日益趋近——被林林总总的组织、体制规训,成为生产链条上无足轻重的环节,离自然越来越远。“包豪斯”乐队、“生日派对”(The Birthday Party,一支签约4AD的澳大利亚后朋克乐队)那种乌云压顶般带着精神病院、谋杀案现场气氛的演唱,是在以否定自我、摧毁自我的口吻发出不妥协的声音,能够广泛触发认同感,也就不奇怪了。
计算机和合成器营造的想象则指向远方。平克·弗洛伊德就特别擅长演绎纯粹、清澈的太空幻境,现在已经成为舞曲界标杆的“宠物店男孩”乐队也有一种特别锋利、冷酷的未来感,所以听起来从不过时,甚至现在在中国又变得时髦了。
我还想提一提在电气化道路上越走越远的“电台司令”乐队。他们的很多歌曲都像科幻小说,试图探讨科技同人性、社会的关系,前瞻性强,但又萦绕着深深的悲剧色彩和无力感——人被技术裹挟其中,挣扎无力。
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塑料假树》(Fake Plastic Tree),歌中的女主角住在一个种满橡胶植物的小镇上,从橡胶人那里买来绿色塑料水壶浇灌自己的橡胶盆景,同居对象也是个精神失常的塑料男人,一切都让她疲惫不堪。歌词写到那种彻底被科技改造掉的世界、那种连假人都不得自由的窒息画面,我觉得特别致命,毫无疑问是诗歌的水准。
某种广义的“英国风格”仍然存在
大约在2005年之后,英国摇滚给人一种“停滞”的印象。至少听众基本没再看到新的风格出炉,新生代很多被标签为特征模糊的“独立音乐”(Indie)或“另类摇滚”(Alternative Rock)。我觉得,这个现象与流行音乐产业的大崩溃有关。
此前,流行音乐产业是一条发现偶像、制造偶像的生产线,超级巨星给公司带来大额利润,优质艺人要成为超级巨星也离不开公司的包装。但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音乐变成了一种即时分享式的流媒体,只要人气高,任何草根背景的音乐爱好者都能以网红身份获得声名,你看贾斯汀·比伯,他最早就是在YouTube上传翻唱歌曲,被业界权威亚瑟小子(Usher)关注后,十几岁就火了。
他们相当于自己包装自己,公司可能扮演的是对立角色,和“对抗资本”“对抗娱乐巨头”这种叙事联系在一起。于是,专业造星生产线存在的意义被解构,当流量代替权威作出评价,乐评人这个行当也被干掉了。而乐评人正是对音乐潮流进行观察、分析的关键角色,也是我们熟悉的那一系列摇滚乐风格、标签的命名者。
2020年,贾斯汀·比伯推出了个人纪录片。
但我觉得,某种广义的“英国风格”仍然存在。就像即使艾米·怀恩豪斯、阿黛尔也玩黑人的东西、唱灵魂乐,和蕾哈娜、碧昂丝她们一比较,就会发现,前者的歌声是思维的产物,而后者的歌声是直接从身体里迸发出来的,带着本能和血性的味道。英式风格是雅致、细腻、时尚的,既有历史文化带来的纵深感,又有高冷、超脱的姿态,甚至还十分擅长自我嘲讽、自我否定。
我不知道这一切是不是和曾经辉煌、在当下走向衰落的贵族趣味有关,但它们无疑和青少年群体的追求高度契合。年轻人渴望让自己从庸众和一成不变的生活中凸显,而脱颖而出的舞台在生活中变得非常个人化,可以通过消费,比如穿衣、听歌之类的个人趣味实现。
所以我觉得很多中国乐队标榜自己“玩英式”并不是偶然现象。“北京新声”(1990年代末与摩登天空签约的一拨摇滚乐队/艺人,包括“麦田守望者”、“鲍家街43号”、“子曰”、张浅潜、“清醒”、“超级市场”、“新裤子”、“花儿”等)那一拨大都自带酷炫气质,大都市的从容、优越感很足,潜台词就是“我最牛叉”。
许多文艺青年也特别吃张亚东作品里那种既苍白又绚丽,既忧郁又自由自在、随心所欲的质感。除了从英国摇滚那里学习录音、编曲、演奏方面的尖端语汇,我想,他们模仿最多的,还是源自英国摇滚的城市化摇滚心态。
✎作者 | 卢楠
“特别声明:以上作品内容(包括在内的视频、图片或音频)为凤凰网旗下自媒体平台“大风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videos, pictures and audi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the user of Dafeng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mere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pace serv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