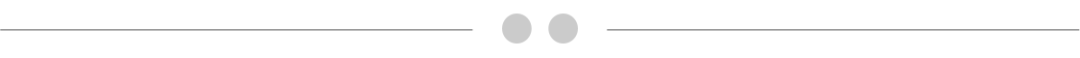哈利·波特让我们迷恋的,是那个近在手边的魔法世界


独家抢先看
8月14日,《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在国内重映,作为疫情后重映影片中人气相当高的一部,不负众望地在上映4天之后就票房过亿。
当然可以说这是大打情怀牌,但自从发现情怀好卖之后,无数厂商早已把情怀牌用了又用,为什么大家会依然买账这部18年前的“儿童影片”?
或者,陪伴大家童年的IP数不胜数,我们又为什么独独对哈利·波特念念不忘?
有人说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是逃离现实的想象乌托邦,在那里骑着扫帚可以上天,抖抖魔杖就能召唤守护神,森林里有人马,海底有人鱼……
但其实,哈利·波特系列之所以有着如此旺盛的生命力,是由于它把魔法世界严丝合缝地嵌入了我们熟知的现实生活,让我们从“麻瓜世界”短暂抽离的同时,又能触摸到魔法背后真实可感的部分。
也许,与现实环环相扣的互文,才是我们在魔法世界里一梦几十年的真正原因。
J.K.罗琳和她的《哈利·波特》,已经是无数人耳熟能详的传奇:30年之前,一位身材瘦削的11岁男孩,突然跃入了正搭乘火车从曼彻斯特前往伦敦的罗琳女士的脑海,他戴着一副圆框眼镜、顶着一头蓬乱的黑发、前额处有一道细长的闪电形伤疤……伴随着车轮与铁轨的合奏,罗琳为这位男孩取名为哈利·波特。
在那之后的时间里,这位男孩从火车旅客的突发奇想,成长为了灵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他的生命世界也化作文字、搬上银幕,陪伴无数人度过了他们的“童年”。
从这个角度上说,很多朋友都会下意识地将《哈利·波特》定位为一部“童话”。但需要指出的是,基于上述这种文类定位的评论,无法充分地解释这样的文化现象:
《哈利·波特》系列小说自问世以来,就同时覆盖了青少年受众和成年受众,以至于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要推出儿童版和成人版两个版本的封面设计;而《哈利·波特》系列电影时至今日也依然魅力不减,吸引着不同年龄段的观众重返影院、重温经典。
在我看来,我们与其沿用老旧的分类惯例,将它视作一篇“童话”,不如将这套无论是篇幅长度还是内容深度都远远超出“童话”范畴的七部曲系列,视作一套“全年龄向”的“奇幻”(fantasy)作品。
1.
魔法世界里的现实倒影
作为一种问世于20世纪中叶的文学类型,托尔金所开创的现代奇幻文学的核心特征在于,它会在“叙事”的同时完成一套“创世”,也就是说,它会在叙述一个引人入胜的精彩故事的同时,创造一套宏大而自洽的世界观设定体系。
《魔戒》系列的中土世界地图
像《魔戒》《哈利·波特》这样的奇幻作品,它们都不仅为影视改编者提供了一套经受过读者考验的故事依据,而且还为商品生产者和广大用户提供了一套丰厚充裕的设定资料库。
而经过媒介赋权的粉丝同人文化与经过媒介融合的文化创意产业,共同运用《哈利·波特》所提供的设定资料库,打造了巨型的产业链条,发布了无尽的用户生成内容,合力造就了21世纪以来最为成功的流行文化品牌之一。
它们既从J.K.罗琳的原著小说当中获得滋养,同时也反过来提升了原著小说的媒体曝光度与社会知名度,助推了原著小说的流行。
那么,在奇幻文艺的脉络当中,《哈利·波特》又有何特殊之处,让它能够成功地凝聚起庞大的粉丝社群,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文化品牌呢?
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世界观设定方式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哈利·波特》的特殊之处。
无论是《魔戒》,还是《冰与火之歌》,它们都创造了一个截然区别于现实世界的架空世界;即使像《纳尼亚传奇》这样的穿越故事,它固然同时涉及现实世界和架空世界,但这两个世界的时空维度也完全不同。
而《哈利·波特》创造的“魔法世界”,却与所谓的“现实世界”处在同一个时空维度,二者并没有截然区隔的分界线。
许多重要的故事发生地点,比如,通往霍格沃茨魔法学校的国王十字车站、通往对角巷的破釜酒吧等等,甚至直接就位于英国伦敦的街头。
故事当中的所有角色,无论是“巫师”还是“麻瓜”,无论是“神奇动物”还是“普通生物”,他们都混居在同一个开放的时空当中。
同那些带有中世纪气韵的架空世界相比,《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更像是将我们所熟悉的现代世界进行了一番奇幻化的微妙变形。
当然,罗琳的世界观设定,无疑有从源远流长的巫术文化、凯尔特文化、基督教文化、中世纪神秘术当中获得大量的素材与资源;但与托尔金等前辈相比,罗琳的最大特色,却是在于她对现代世界所作的戏仿与变形。
例如,魔法世界会按照现代世界的民族国家疆界来划分行政区域,每一块行政区域都有一个名为“魔法部”的政府机构,这个政府机构有着分工明确、设置完备的科层组织,依照规范化的法律制度实行内部治理,并与其它国家的魔法部展开国际合作。
相比起中土世界、维斯特洛大陆上的封建王国,这无疑是一套更接近于现代社会的政治体制,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J.K.罗琳对于现代政府的一种带有戏谑色彩的模仿。
除此之外,《哈利·波特》的很多重要的世界观构成元素,比如国际巫师联合会、威森加摩、阿兹卡班、古灵阁、圣芒戈、对角巷、《预言家日报》,也都可以视作罗琳对于现代社会的国际组织、法庭、监狱、银行、医疗机构、商业街、大众传媒的戏仿。
而在罗琳的一系列设定当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霍格沃茨魔法学校。
作为《哈利·波特》最为重要的故事发生地,霍格沃茨的相关设定,既是对魔法学习这项超现实活动进行了现实化的处理,同时又对现代学校这个日常生活空间进行了奇幻化的变形。
罗琳的文字在“现实化”与“奇幻化”之间保持了一种微妙的张力,在激起读者亲切而熟悉的生活经验的同时,又通过这种张力刷新着读者的审美体验。
2.
奇幻设定的现在进行时
《哈利·波特》的读者可谓类型多样、构成多元,但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依然有一个共通之处,那就是都曾经有过或者正在经历现代校园生活。
而罗琳对于“现实化”与“奇幻化”的巧妙把握,一方面能够持续地引发读者的沉浸感、代入感与共鸣感,另一方面又为现代校园生活增添了许多令人惊异、充满神秘的奇幻色彩。
这两方面效果的微妙叠加,让霍格沃茨对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构成了持久的吸引与召唤。
茱莉亚·萨瑞克(Julia Saric)曾经对《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与《魔戒》的“中土世界”进行过比较研究,他认为罗琳的幻想形式与托尔金创造“第二世界”的形式不同,罗琳的幻想是一种“归化式幻想”(Domesticated Fantasy),也就是“把我们熟悉的东西奇幻化”。
斯蒂芬·巴菲尔德(Steven Barfield)则将《哈利·波特》与托尔金、茨维坦·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和罗斯玛丽·杰克逊(Rosemary Jackson)三位奇幻文学理论家的三派奇幻理论进行比较,他认为《哈利·波特》不同于其中任何一派,进而将《哈利·波特》的奇幻形式命名为“讽刺性奇幻”(Satirical Fantasy),也就是作品“以戏拟的形式指向现实世界的缺陷”。
但在这里,可能更为合适的是借用后现代主义哲学家让·波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的概念,将《哈利·波特》视作一部“仿真的超级现实主义”作品,将《哈利·波特》创造的魔法世界视作一个混淆了真实与想象之界限、弥合了技术与巫术之界限的仿真世界。
在这个世界中,“童话”或“奇幻”的“魔法”经受了现代性的异化,或者说,现代文明的技术发生了魔幻化的变形。
我们可以将魁地奇作为例子,这项令魔法世界的巫师、《哈利·波特》的读者如痴如狂的运动,其实就是对现代社会的多项体育运动的戏仿与拼贴。
魁地奇的规则糅合了足球、篮球、棒球、橄榄球、躲避球等我们熟悉的运动。
也正因如此,世界各地的哈迷学生可以根据麻瓜世界的物理规则,将这项由巫师骑着扫帚在天上飞行的运动,改造为麻瓜提着扫帚在绿茵场上奔跑的运动。
而飞天扫帚的相关设定,那些由专业扫帚制造商生产的内置有“振动控制”等性能的价格不菲、不断升级的名牌飞天扫帚,则会让我们联想到耐克、阿迪达斯等品牌的运动装备,以及F1方程式赛车。
而罗琳关于国际魁地奇联盟、魁地奇职业联赛、魁地奇俱乐部的球迷文化以及每四年举行一届的魁地奇世界杯的描写,更是会让我们直接联想到现实足坛。
另外,在我们的现实世界中,不但有麻瓜魁地奇,而且还有一些人真的尝试借助高科技来还原巫师骑扫帚的体验。
比如,在华纳片场和环球影城,只要借助电动扫帚、绿幕技术与CG技术,或是借助云霄飞车与AR技术,你就可以获得自己骑着扫帚飞过伦敦街头、飞过霍格沃茨的实时影像。
在这里,科技成为了魔法目标的一种另类实现手段。二者似乎是可以相互替代、殊途同归的。
3.
科技与魔法的互文,
成为了撬动现实的支点
举完魁地奇的例子,我们再来看《哈利·波特》系列小说中的两句耐人寻味的话。
首先是《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中的一句话,当哈利在骑士公共汽车上,阅读《预言家日报》关于小天狼星布莱克依然在逃的新闻报道时,他读到了这么一句话:“麻瓜们被告知,布莱克携带一把枪(一种金属魔杖,麻瓜们用来互相残杀)。”
《预言家日报》的这份表述其实也向我们提示出,在《哈利·波特》的故事中,使用魔法的“巫师”与利用科技的“麻瓜”,他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语言方式其实是具有可通约性的,甚至可以说,二者是有异曲同工之处的。
还有一句话来自《哈利·波特与火焰杯》。在《霍格沃茨:一段校史》——也就是霍格沃茨魔法学校的官方校史里,把电力、计算机、雷达等麻瓜的科技发明都称作“麻瓜使用的魔法替代品”。
我们可以看到,在魔法史写作者的巫师中心主义的历史视野当中,科技被视作魔法的替补。
当然,我们也可以从麻瓜的视角,将绝大多数能够在现代全日制寄宿学校里通过上课、做作业、做实验、写论文、考试等步骤逐步习得的巫术,视作现代技术目标的另类实现手段。
《哈利·波特》构建的这个“魔法异化”或者说“技术魔化”的仿真世界,可以提醒我们换个角度来思考魔法与科技之间的微妙关系:
一方面,我们常常会说,现代文明是经由科学世界观对于巫术世界观与神学世界观的清除和取代,才得以建立起来的。
但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通过所谓的“驱魔”和“祛魅”建构起来的现代社会,实际上是经由一个殊途而同归的进向,利用技术来实现并替换魔法/巫术的目标。
现代科技的发展乃是“魔法技术化”的过程,是技术替补巫术的过程。
另一方面,在当代后工业社会的大众文化产品中被“人为地复活”的巫术,也就不可能回归它的起源,而只能是在历史性的延宕与变异中被作为技术的仿真与替补,投射着置身于后工业社会与新技术革命进程中的人类对于“技术魔法化”的体验、想象、迷恋与焦虑。
就此而言,《哈利·波特》这个仿真游戏所创造的“魔法——现实”意象场所,并不是现代“成人”为确证自我、寻求庇护、获取抚慰而构想的“童话净土”,不是与现代性世界二元对立的“神秘的原始思维的世界”,也不同于托尔金幻想的纯架空的“第二世界”,而是一个弥合、混淆界限的魔法异化/技术魔化的仿真世界。
罗琳正是通过对这种仿真世界的精心雕琢,终于觅得了可供撬动壁垒森严的“儿童文学/成人文学”的现代性建制,打开书写现实、探讨善恶的深层空间的“阿基米德支点”。
作为一部以正邪对抗为基本框架的奇幻文艺作品,《哈利·波特》包含着一套灾难与救赎的情节结构。
其中的灾难蕴含着作者对于伏地魔及其“魔法即强权”的政治实践所代表的以纳粹法西斯为历史原型的技术极权展开的反思和批判。
而哈利以“爱的魔法”与缴械魔法来对抗伏地魔的弥赛亚式救赎,则寄寓了作者的美好愿望:以爱的力量对抗死亡驱力,以追求平等、包容多元的态度反对偏见与歧视,以本真的“向死而生”的生存论筹划来反抗技术系统的异化。
这使得《哈利·波特》现象成为我们时代的文化矛盾的一个绝佳的象征。
现代社会的基本悖论就在于技术系统的现代性与人的解放的现代性之间的悖论,而看似吊诡的《哈利·波特》现象,正是象征这一悖论的生动的寓言。
“如果你生于1985到1998年之间,请记得你的霍格沃兹入学通知书之所以没寄到,是因为伏地魔抹去了政府文件中这期间出生的麻瓜巫师记录。”
“特别声明:以上作品内容(包括在内的视频、图片或音频)为凤凰网旗下自媒体平台“大风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videos, pictures and audi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the user of Dafeng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mere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pace services.”